乘載臺北人三十年記憶的中華商場
從黑手打鐵的赤峰街到文青的赤峰街
2022年全世界最期待的建築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曾經荒置的公務眷舍審計新村,搖身成為臺中最受歡迎文創景點
從孩子日常生活的視角,將鄒族文化傳統融入設計的阿里山達邦國小
五個建築場域,
五段文化歷程,
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集結了建築學者殷寶寧近年來在建築、設計與文化領域的研究與寫作。看似獨立成篇,但共同貫串的,來自於對文化深層的關注與提問。
殷寶寧以地域為經,年代為緯,在建築與文化的交織論述中,觀察設計如何回應使用者的想像與實境。最初以中華商場啟章,在於該建築承載了臺灣在戰後現代化過程中,追求在城市景觀與建築表徵上的現代性之夢。接著來到捷運中山站與雙連站之間的赤峰街街區,曾經是黑手油氣產業聚集之處,而今反差萌地構成文青青睞的文創聚落。
再往北邊走一點,回到劍潭與基隆河前世的探索中,一座明星建築要如何轉身變為一座演藝廳呢?離開臺北,臺中的審計新村,創意工作者的群聚及其構成的創意聚落,帶動區域活化,具體回應了設計文化不僅是一個過程,更具高度能動性的價值。繼續往南到了北回歸線,百年達邦國小重建,應該長成什麼樣子?「設計」如何作為一種傳遞文化與歷史重量的媒介?建築生產要如何滿足這個社會單位,並且傳遞出具鄒族族群主體意識的文化形式?
透過這些詰問,我們在殷寶寧的文字中飛越臺灣的百年建築構成,以鳥瞰的視角,踏實的取材,照見設計在建築與文化之間以何樣的角色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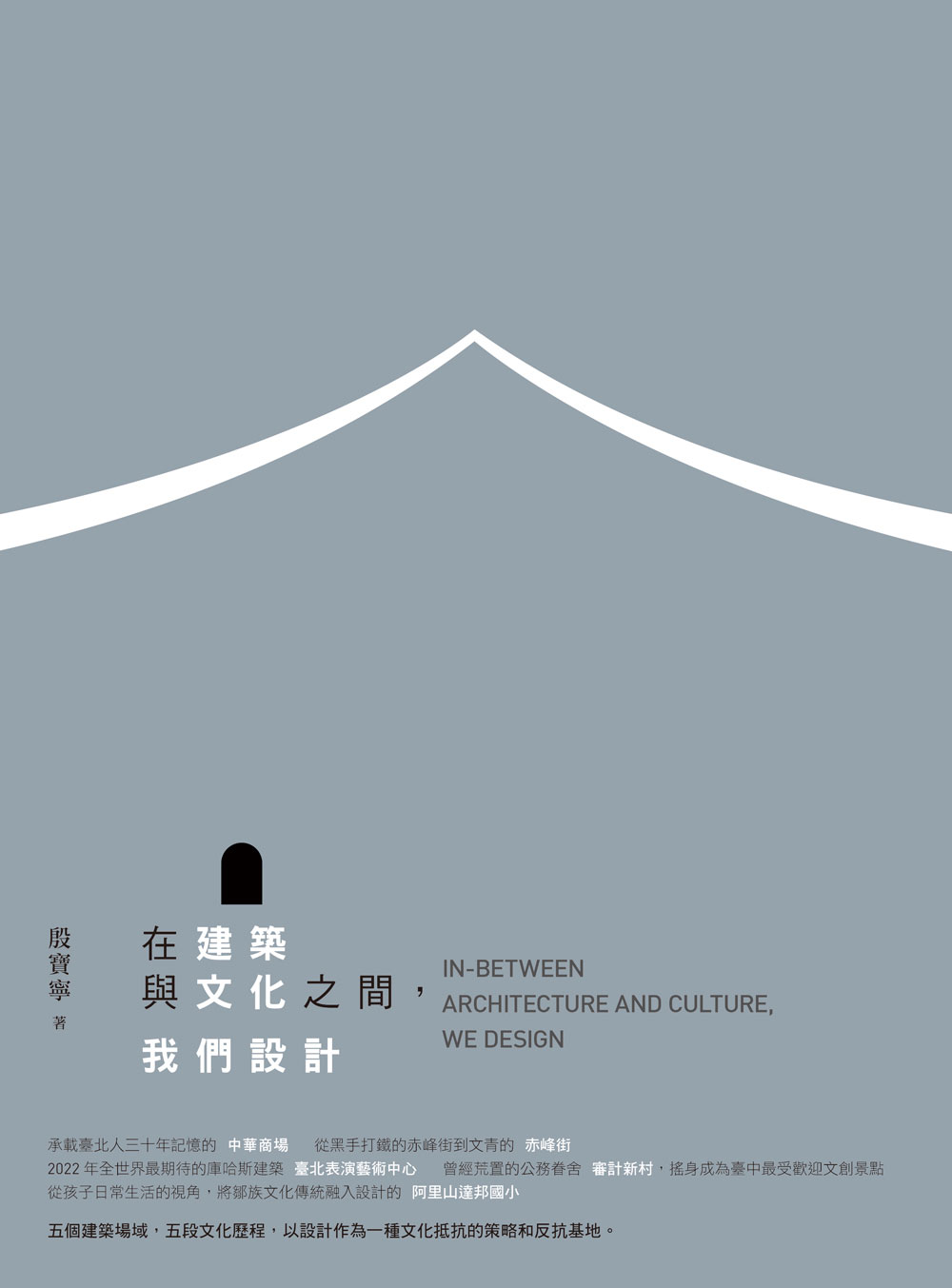
好評推薦
處在城市快速變貌的時代,我們需要殷寶寧這樣的城市研究者。一方面為城市召喚失去的記憶,也為城市的高速發展擴張,提出具有理想性的思考方向與設計方式。———于國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給了我們一個如是犀利而溫柔的提醒:這片土地的人民該如何不卑不亢地瞭望與實作另類的想像,嘗試設計建築出能貼合島國肌理又促成文化改變的永續生活空間。———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研究案例取樣多元,涵蓋多個具有代表性的地域街區與文史建築。作者殷寶寧細密爬梳城市變遷的治理歷史,為讀者提供相關建物、街區的地誌文獻,甚而擴及全球化底下文化輸出與美學轉移的政治經濟脈絡。———陳正菁|浮光、春秋書店創辦人
殷寶寧簡介
殷寶寧生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現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專長領域包含建築與文化研究、文化資產與博物館、性別研究等。
曾任職於教育部,參與921震災校園重建工作;曾任職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副總臺長、真理大學,並陸續於淡江大學建築技術學系、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等教學單位擔任兼任師資。
近年出版專書包含:《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淡水文化地景重構與博物館的誕生》、《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我城故事:大稻埕街區生活書寫》,《知識展示重構:博物館建築空間與觀眾經驗》,並主編專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導論》。
參與創設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建築改革社、現代建築學會、文化資產學會、臺灣老城水岸文化協會等民間專業社團。曾任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現任臺灣老城水岸文化協會理事長。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目錄
推薦序
城市的懸念──于國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搭建一座改變建築思維的橋頭堡──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記憶與想像:生產與剩餘的城市地景──陳正菁|浮光、春秋書店創辦人
序 設計:在建築與文化之間
第一章 建築現代性的想像及其終結:中華商場的誕生與死亡
中華商場的誕生:一個現代性的想像方案
——中華商場史前史
——為何是「中華商場」?
——中華商場的營造與落成
中華商場的建築空間生產與文化形式分析
——趙楓與中國興業-趙楓建築設計風格初探
——中華商場的空間生產與建築風格分析
建築量體、屋頂形式、外觀立面、開窗方式、中式語彙
中華商場的死亡:現代性的終結或再生?
結論:永不衰竭的夢?
第二章 都市生活與街道記憶考現:重描臺北市赤峰街
赤峰街:空間的生產
從有機發展到城市規劃:從清領以降到殖民統治
——聚落有機發展的城市軌跡:從清領到日治時期
——臺北市都市計畫的形構力量
都市計畫與公有零售市場政策、公學校、公園綠地的出現
——有機發展與都市規劃下的空間生產:赤峰街
從都市規劃到產業空間生產:戰後赤峰街與城市有機發展軌跡
——違建與佔用下的街道景觀
——視覺清理與城市景觀打造:有限的空間實踐介入
——產業群聚的歷史累積:朝向生產空間之轉向
街道的再現空間:文學與新聞報導中再現的赤峰街
——《赤峰街5號的那些事》
——新聞報導與再現空間:性別與階級視角
性產業與女性生活處境、銷贓、
結語:街道為何重要?
第三章 全球化下都市再生與名牌建築——庫哈斯與臺北藝術中心
設計文化(Culture of design)與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
中山北路-劍潭-基隆河舊河道都市開發歷程
臺北藝術中心開發案與周邊房地產
庫哈斯(Rem Koolhaas) OMA團隊及其專業論述
建築量體與士林夜市的戲劇性言說
第四章 建築變身演藝廳?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行動者網絡研究
研究對象與分析取徑:行動者網絡理論
——臺北藝術中心:多元行動者作用下的產物
——行動者網絡理論
臺北市政府的文化治理軌跡概述
——地方與中央文化治理競逐的想像
——自行開發或邀請民間投資:從財務角度詮釋文化政策想像?
——「文化引導都市再生」與「城市品牌行銷」的文化治理核心作用
建築設計團隊視角
——為何來臺灣參加國際競圖?
——建築設計的重要概念
——建築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者:「被」缺席的使用者
——建築設計團隊提出的其他觀察
非人行動者:建築物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的專業詮釋
——經營使用團隊何時(應該)可以進場?
——表演經營團隊的空間經驗與見解
——北藝中心經營團隊的自我定位與期許
第五章 審計新村變身記:城市文化治理與創意場域形構
前言:審計新村變身記?
從網絡治理到「創意場域」
——從治理到網絡治理
——從創意城市到創意場域
從臺中地區五大村到審計新村的誕生
——「審計新村」、公有眷舍與中臺灣發展歷程
——審計新村空間構成概述
多元網絡治理實踐下的審計新村變身故事
——都市研究專業者引燃的熱情火種
——社區組織工作者的網絡化角色:如何建立積極溝通橋梁
——教育部、大學的角色與力量
——國有(非公用)財產的活化議題
——地方政治作用與選舉因素的影響
第六章 以設計人類學反思學校設計過程:阿里山達邦國小個案研究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分析架構
臺灣戰後教育體制與校園空間變遷圖繪
個案分析:達邦國小
——達邦國小個案概述
——設計目標-校園成為具鄒文化自明性的族群空間認同所在
——參與式設計過程與設計轉化
——設計策略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序
設計:在建築與文化之間
建築、設計與文化這三個詞彙可說是傍身日常。以長期浸淫日久,遂有近廟欺神之疑:似乎從未認真反思這幾個語詞,或者說,疏於端詳考掘。以為自己應該是知道的,但專業領域翻新速度遠遠勝於個人學習追趕的腳步,長此以往,自以為熟稔的老朋友,彷彿也換了個樣貌,讓人不禁對自己起了疑心,我,真的清楚這些概念訴說著什麼嗎?這幾個我以為不需要太追根究底的詞彙,真的可以如此輕易跟我好好天長地久廝守?
「文化」可能是這三組中涵括範疇最為廣袤的。人類生活中的一切軌跡都可以統合在「文化」中;「建築」為表徵或再現文化的物質展現。而「設計」則是有目的性的工具性過程,同時具有動詞與名詞的意涵,既為了要解決特定問題與需求,也是展現獨特價值的方案、計畫或成品。而在抽象層次上,設計也是轉化或象徵文化的某種途徑。
「文化」在中文的語境與「人文化成」有關,以別於人類和其他物種的差異所在,強調經由特定的教育、教化與文明的薰陶與養成,能夠形塑為穩定人類社會恆久安然運作的內在力量。這股內蘊力量表現在外,成為藝術美學的形象化物質表達,經由各種藝術作品來抒發這種無以言表的本質能量。
在西方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藝術與文化通常也是緊密相連的──藝術所寓意的美學、品味與豐盈富庶,被視為文化的。
設計學研究者裘利業(Guy Julier)指出,設計的歷史面臨兩個方法論上的困境。一般我們所熟悉的,在書店裡美美彩色書頁裡,或者是暢銷的書本雜誌所討論關注的,乃是所謂「大眾設計歷史」。這類設計史的切入觀點,聚焦於個別設計者的產出,強調設計風格;這些引發大眾目光與喜愛的物品,從建築、家具設計,到物件與平面設計均得以大行其道,造成話題或銷量利潤,但卻往往忽略設計過程,及其可能對社會產生的衝擊。
另一方面,學界的設計史學家採用1990年代的物質文化研究取徑,則試著從另一條路徑,想解釋人們日常生活裡的各種物件的重要性。換言之,不同於大眾設計歷史的視角,採取物質文化觀點的史學家,不再沈溺耽美於這些物件的形式、風格、色彩與造型等等,而是關注於消費者/使用者如何看待或運用這些物件,以及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或改變(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v-vi)。
這樣的張力或許也可以解釋,何以「設計」產品雖具有高度物質性特徵,有其所對應要解決的課題。但在臺灣的社會情境中,往往多停留在對表面形式風格與視覺表現的討論,並以此來論斷設計存在的價值與市場競爭力。
「設計」同時是一個動詞也是名詞。從定義上來說,乃是為解決面對特定情境與條件時,所遭遇之問題,或達成某種目的之計劃、發明的活動,或完成特定成品產物的過程。像是完成一份計畫,或是製造出一個成品。而所謂的「設計文化」則可以理解為,所實踐出來(practiced)的品質,此意指是已經進行過的方式,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經歷、感知、理解與執行。此外,由於要解決的問題或面對的條件是具高度在地性的,例如,於設計師所處的工作系統、知識與社會網絡狀態緊密連結,也與其面對的政治權力、經濟與論述系統結構高度相關(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5-6)。如此一來,解析特定社會情境條件中的設計文化,有助於解析特定社會中,設計生產的條件樣態。為此,裘利業提出五種有助於建構起經由設計文化來解析設計與社會關係的論證觀點,分別是:一、以設計文化作為一種過程。二、以設計文化做為具脈絡訊息的實踐。三、將設計文化作為一種組織的特徵。四、以設計文化作為一種能動性。五、設計文化作為一種普遍卻分化的價值(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6-8)。
這些不同的論證觀點與切面,共同指向將「設計文化」視為研究對象之際,實乃同時觸及了日常生活的物質與非物質面向。在其中,藉由形象、文化、形式與空間等元素相互構連,成為得以建構起設計文化的研究切點。這使得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課題變得日益重要──視覺轉化為資訊符號快速地傳遞流通,擷取、連結或扭曲、轉用,成為支撐設計文化產生作用的關鍵,並得以激發價值、信仰、行動、結構與關係,且足以反過來繼續構成新的設計文化。
隨著視覺資訊變得短暫而即時,文化所仰賴的基礎也逐漸提升。日常生活裡,「設計」作為一種自覺的特殊表徵,已日益隨處可見,拓展了視覺價值的立基範疇。如同裘利業引用拉許(Scott Lash)所言:「現在的文化是三維的,就像視覺或文字一樣是有形的,圍繞在我們身邊,以一種再現的形式居住並存活於分離的疆域裡,而不是在其中與我們偶然相遇。」(Lash,2002:149,轉引自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15)。拉許以「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為母題所提出的資訊批判,直言當前乃是「資訊即社會」的時代,資訊即權力。昔日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下社會權力關係,諸如對階級剝削的批判,早已將權力讓位給擁有資訊與溝通工具的群體。那麼,要對抗這樣的權力關係,也必然具備掌握資訊的能力:即時地、非線性的,能漫遊於資訊流動與網絡之間(Lash,2002)。
想像一下,在拉許所描繪及構築的,以資訊來相互建構、彼此理解的世界裡,資訊流動掌理了一切。文化與資訊或許成為同義詞?文化不再只是視覺文化傳達訊息的純粹再現或敘事之一,是個等著被定義與探討的客體;與此相反地,文化制訂、定型、傳輸、容納或是收回資訊。如此一來,設計不只是創造出可以被使用的視覺物件,也在此視覺化的物質世界中,結構出讓物件得以相遇的系統(Guy Julier,鄭郁欣中譯,2009:15)。
在資訊社會中,從設計、文化到資訊所勾連起的等號函式,如果代換為「建築」呢?
關華山教授新近出版專書《建築學是什麼》,提及王明蘅教授演講時,以四個面向來討論建築──分別為「圍閉空間」(enclosed space)、「社會單位」(societal unit)、「物質結構」(material structure)與「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 (關華山,2021:21-23)。這四個面向的確點出了「建築」同時具有抽象與實質的特徵,滿足日常生活實用需求,以及精神情緒感受的價值層面,是個人維繫生命所需,但也是社會集體理解與共識所在;建築本身由其圍塑之虛體空間來達成被寄寓的功能,仰賴技術理性的結構系統,確保建築本體的穩固,但空間表現於外的文化形式與美學符號,在象徵層次傳遞著人類社會的相互理解與溝通。
然而,前述設計學者裘利業所提醒的方法論困境,及二元對立的緊張關係,同樣存在於「建築」──我們有太多日常生活遭遇的需求與課題,必須透過「建築」這個物質性的存在來支撐、完成。然而,這個部分被關注的層面相對稀少,而被描繪或呈現得無趣,遠不及大師名作的各種爭奇鬥豔來得吸引目光,創造眼球經濟,累積文化資本。
文化基礎設施可能就是這樣的產物。一方面,必須藉此已完成各項被期許的文化資源/支援工作。諸如提供在地所需的藝文場館、表演空間,推動在地藝術教育,培養地方文化紮根,支援當地藝文團體,滿足市民日常休閒文化生活需要。這些看起來平凡而不足為奇的論述,在臺灣其實發展得也還沒有太長久的時間,建構得相對完整或許也還需要一點時間,軟硬體皆然。
然而,相較於需要綿長抗戰而持續鋪設的文化基礎設施的推展腳步,明星建築師創造的名牌建築,在臺灣的每日生活經驗裡,可能發展的速度還要更快些。或者,這兩者之間有著合流的機會?劍潭捷運站外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或許就是這樣的故事?只是,著迷與明星建築師的世界級名作,藉此滿足臺北市想躋身世界城市舞臺的慾望,我們忘了這些文化基礎設施的建構,乃是為了保有並傳承我們的文化,建築之餘,摧毀與遺忘同行。
在這中間貫串起來的線索一是時間/歷史,一是倫理。或者,還有根著地域的認同其間。
當我們如此宣稱「資訊即社會」或「資訊即文化」時,回到主體經驗感受來看,是否能夠如此輕易地接受/承受?其間的縫隙或皺摺,或是足以構成一點點噪音聲響的干擾,正是來自於主體身體記憶中的百轉千迴,難以驟爾抹除。
舉例而言,我們經常聽聞所謂「美與不美、見仁見智」;但很多時候,衝突乃是來自於既有的視覺經驗受到干擾或挑戰。置放於個人層次,看似歸因為個人化尺度的美學偏好,但拉升至集體記憶範疇之際,歷史性的沉澱積累,相當程度地支配了美感經驗而不易察知。當我們習慣於四平八穩,富麗堂皇的殿堂式博物館建築,遇見街角博物館的社區型尺度,挑戰了人們的理解與認知。而奇異形狀且自以為具美學論述獨佔性的美術館建築,企圖簡化為美感經驗的個體差異,忽略人們美感經驗中的倫理成分。倫理與歷史感受經常相互交織、彼此作用。前述舉例東施效顰的美術館引發熱議,除了挑戰一般人經驗中的美術館建築印象外,與周邊環境的不協調,更是臧否美感與否之先。
時空之間,前述拉許所描繪,三維的文化,立體地環繞於我們身邊。但這段生動鮮活的文字中,攸關主體經驗的歷史記憶、美學倫理與地域認同,均靜靜地被擱置著。
正是由於建築、設計與文化彼此之間的糾纏難解;也正是因爲時空之間,牽動社會變遷、經濟條件、歷史脈絡與文化條件,建築生產與設計文化也隨之變異著。而從「資訊即社會」到「資訊即文化」,卻很難解釋,何以建築、設計與文化之間,難以順暢無縫接軌,總是充滿各種斷裂、隙縫與皺摺。尋覓與理解這些斷裂、隙縫與皺褶所在,大概就是組織這本書的內在企圖吧。
在本書中,為研究者近年來在建築、設計與文化領域的研究與寫作。最初以中華商場啟章,在於該建築承載了臺灣在戰後現代化過程中,追求在城市景觀與建築表徵上的現代性之夢。然而,這個當初為了解決龐大社會移民的住宅需求困局,採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現代建築風格,在機能上結合居住與商場,帶給臺北市民愉快的現代化夢想國度,累積了無以數計的市民記憶。但其消亡同樣來自另一股現代化論述──現代化的都市應該要有捷運、應該要有林蔭大道、不應該讓火車在地面上跑。鐵路地下化、捷運開挖、打造中華路林蔭大道,這些現代化的都市景觀工程,容不下市民集體記憶中的昔日之夢,而最終夢碎,只能在吳明益的小說和同名電視劇中,引發集體鄉愁發酵後的夢囈多語,而醒覺於我們終究不是「我們」?
承接著中華路在城市景觀中,以線性街道架構起來我們的城市意象、記憶與情感。另一條城市軸線──中山北路,於近年來被置換為捷運北淡線後,赤峰街擔負著從大稻埕串接到捷運中山站的另一段中介。
捷運中山站與雙連站之間的赤峰街街區,構成近年來受文青青睞的文創聚落。曾經是黑手油氣產業聚集之處,在媒體上被解讀為汽車銷贓之所,卻由此反差萌般地,轉身販賣這些過往的階級差異編織的鄉愁,以文化引導都市再生的樣板規格,成為臺北市政府觀光文創與文資保存三位一體的政策櫥窗。
再往北邊走一點,我們在圓山與劍潭之間,循著城市再生的思考,這回連結上的是全球化情境下,企業城市(enterprise city)的發展企圖,與明星建築師的亞洲馳騁野心。回到劍潭與基隆河前世的探索中,從地域和歷史記憶出發,建構起一點點重新閱讀名牌建築的建築詮釋。
但故事還沒有說完,似乎沒有人認真地探問過,王明蘅教授所提出的建築四面向中,圍閉空間、社會單位、物質結構與文化形式這幾項,要如何有機地整合起來?在此的提問是,一座明星建築要如何轉身變為一座演藝廳呢?研究者試著挪用行動者網絡研究理論,將建築視為其中的重要行動者之一,為網絡作用中的要角,構成整個行動網絡的「強制通行點」。透過訪談方式收集資料,既企圖檢視官方文化治理思維的轉譯過程,回應臺灣盛行的蚊子館論述,更意圖找到解析「建築」的新取徑。
從臺北再往南一點。臺中的審計新村,以長期推動創意市集,被詮釋為官方閒置宿舍群轉型的正面案例。既具有文化政策豐碩治理成果的高度正當性,對財產管理部門言,更是委外經營的成功樣板。昔日穩定安居的眷舍,精省閒置廢棄後,儼然只是國家登錄在案的有形資產,得以改頭換面,關鍵力量即來自於研究者所關切的,設計推展過程中的諸多縫隙斷裂,誘發都市空間重新縫合的動能。創意工作者的群聚及其構成的創意聚落,帶動區域活化,具體回應了設計文化不僅是一個過程,更具高度能動性的價值。
繼續往南到了北回歸線,阿里山鄒族達邦部落。這裡有著日本時代最初建立的國民學校體制。「開山撫番」「教育開化」的殖民意圖下,達邦國小迄今超過百年的歷史。無庸置疑地,學校是傳承歷史與文化的基地,但也可能成為殖民剝除族群集體記憶的所在。那麼,如此一來,擔負著孩童學習族群文化的學校,應該長成什麼樣子?「設計」如何作為一種傳遞文化與歷史重量的媒介?建築生產要如何滿足這個社會單位,並且傳遞出具鄒族族群主體意識的文化形式?
本書的每一個章,看似獨立成篇,但共同貫串的,來自於對文化深層的關注與提問。透過設計與建築的中介,挪用設計文化與建築理論相關連的各種理論視角,並非意圖建立任何系統性地、有所框架的理論觀點;而是與此相反地,意圖更細微地檢視前述這些概念的多元樣貌,以及選煉其彼此連接之間,必然出現的斷裂、轉折、雜音、縫隙或皺褶,端詳審視權力運作過程,可能出現的各種軌跡,以設計作為一種文化抵抗的策略和反抗基地。當然,負隅頑抗前,高解析度地辨明對手應是提出對戰策略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關華山(2021)。建築學是什麼,臺中:臺中市建築師公會。
Julier, Guy,鄭郁欣中譯(2009)設計的文化,臺北:韋伯文化。
Lash, Scott(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購買連結
博客來購買《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內文樣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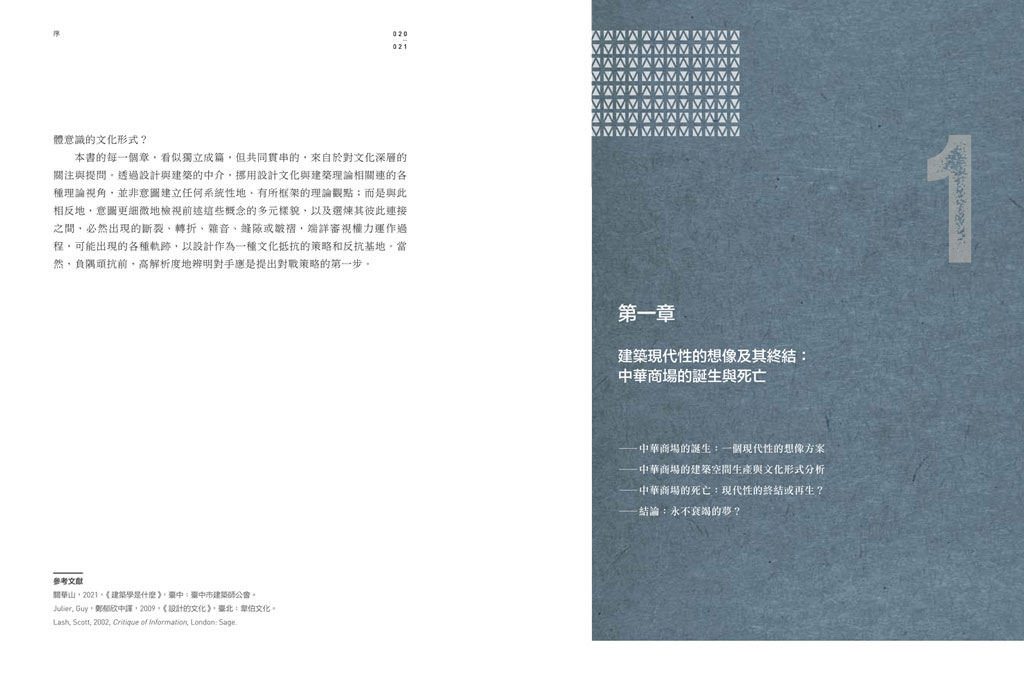
《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書摘
庫哈斯與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建築量體與士林夜市的戲劇性言說
「城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為當前各國城市普遍面臨的挑戰。全球化潮流下,城市乃軟實力競爭的關鍵場域,在城市行銷與品牌建構的強烈意圖作用,以文化與設計引導城市再生(culture and design-led urban regeneration)的發展模式成為都市治理的主流。兼具老舊與歷史城區活化、提升整體生活品質、以文化魅力帶動地方經濟再生的空間計畫,卻經常往大型文化建設計畫發展轉向,挪用城市文化行銷模型,掏空其文化內涵深度,忽略本地居民的生活感知與環境品質需求;訴求全球知名度的建築師,以視覺景觀的名牌建築(signature architecture)所承載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支配性美學,作為打造城市自明性的速成法,滿足觀光客凝視(tourist gaze)(Urry, 1990/ 2002)之際,是否對在地居民的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與認同產生衝擊?另一方面,這些大量來自西方的知名建築師進軍亞洲城市,其造成建築表徵與都市景觀的高度表現性,是否可稱為另一種文化帝國主義?而建築評論家主張以「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Tzonis, and Lefaivre, 1981; Frampton, 1983)作為對抗現代主義及當前全球化普同性(universalism)取向的見解,是否能夠回應亞洲城市面臨的強勢文化入侵?
臺北市政府自馬英九市長任內,宣布計畫投資45億元 ,興建「臺北藝術中心」(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re,簡稱北藝中心,TPAC) 。(編按:本章談及市政府原規劃設計案時將以原名稱「臺北藝術中心」表之,其餘則以現有定名「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或官方公布簡稱「北藝中心」稱之。)該計畫定位為具有文化產業、觀光遊憩與城市行銷等面向,即是以文化為名的開發案。此案基地位於基隆河廢河道土地上,緊鄰劍潭捷運站;原為士林市場遷建的臨時攤商賣場,此開發案牽動周邊劍潭與士林夜市環境的都市更新課題,以及企圖以文化引導都市再生的治理模式。2009年1月,經過國際競圖,由荷蘭裔的明星建築師(star architect)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團隊取得設計權。
庫哈斯團隊2008年設計北京中央電視臺引發高度關注的鋒芒,其首次登台或許意涵著臺灣的城市與文化治理企圖在名牌建築全球化的潮流中擁有發言權;加以庫哈斯團隊長期在都市與建築議題上的積極論述,深諳如何以具高度表現性的建築形式,挑戰都市文脈、環境景觀、在地美學等課題,且每每形成具爭議性的城市文化議題。本章試圖以庫哈斯團隊與「臺北藝術中心」建築案為例,思考全球化發展趨勢下,都市治理、城市行銷與名牌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
庫哈斯OMA團隊及其專業論述
庫哈斯 出生於荷蘭,在倫敦與紐約兩地接受建築教育,後以紐約、阿姆斯特丹兩地為基地發展其建築實踐。庫哈斯在當前具全球性知名度的建築師中,生平背景與經歷較為特別的是,雖然出生於荷蘭鹿特丹,但在十歲之前,他都是住在亞洲的荷蘭殖民地印尼度過。回到荷蘭後,最初是攻讀新聞採訪,後對電影編劇產生興趣,曾編寫過幾部劇本。相較於其他建築專業者,除了在全球各地接受委託案,庫哈斯的專業實踐模式更著力於建築理論的挖掘與論述拓展。其最初在業界受到關切,並非因為建築作品,而是以其專業論述與出版贏得各界關注 。例如其所著的《狂譫紐約》(Delirious New York: A Retroactive Manifesto for Manhattan )(Koolhaas, 1979)、《S, M, L XL 》(Koolhass and Bruce Mau, eds., 1995),探討在當代急速而全面的都市化現象,建築已經無可逃脫地、成為難以在如何地訴說、或展現自我的存在。他提出「通屬城市」(或譯作「同質城市」)(generic city)、(Koolhass and Bruce Mau, eds., 1995)的概念,凸顯出全世界都市化的蔓延現象,只是製造出完全沒有差別的城市,也脫離了過去的歷史與經驗。這本書幾乎可以說是庫哈斯將其論述焦點,從20世紀的曼哈頓城市景觀,移轉到建築與都市規劃的場域(Hajer, 1999:140)。事實上,庫哈斯一再著眼於對城市的討論,乃是其清楚地點出,「城市」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催動的發展基地,城市的規模及其發展趨勢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與之相比,建築相形失色,不僅在尺度上難以取得優勢與目光,面對城市裡的摧毀性創造,建築的生命週期顯然是稍縱即逝、如白駒過隙一般。
故放在城市發展與建築兩者關係來看,庫哈斯的主要論述見解有兩個較為關鍵的分析角度,其一為庫哈斯對當代、全球化下都市發展趨勢之於建築的正面衝擊的持續倡議;其次則對此情境下,建築師這個專業實踐面臨的嚴峻挑戰,或說,其可操弄與縱身之處。
庫哈斯在《狂譫紐約》書中以曼哈頓都市景觀召喚出的迷戀(obsession),讚頌曼哈頓是「城市中的城市」(cities within cities),提出「壅塞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的論點,沉浸於對城市高密度、速度、擴張等失控卻又有其自行運作的內在邏輯與驅動力之討論。他反對桑奈特(Richard Sennet, 1977)所提的古希臘雅典城市「公共人」(the public man)的思維,認為那是靜態而過時的城市文化模型;反之,從城市尺度、密度的思維來理解,每棟建築以其摩天樓、大量體所呈現出的狂譫狀態,看似混亂的城市,反而成就出令人沉迷不悔的各種可能性。也因此,對於歐洲城市既往所意涵文化與城市傳統的懷舊風,他提出的看法是:
「人們必須從一成不變的想法中解放出來,而非代表必須放棄新舊兩者間關係的建立。歐洲註定會成為全世界通用的巨大觀光機器。她必須要能夠展現文化。而這亦是我們必須頌揚當代的原因之一。因為在我們對於歷史都市的關懷和考慮其用途上,這世界觀光中心的角色必然會占據最為重要、明顯和決定性的分量。所以重要的是去平衡這樣的看法,而非認定這兩段不同的都市發展時代必會斷然地分裂而且無從比較。」(夏思藍,2003: 100-101)
延續這種對城市發展趨勢的長期觀察,當時急速崛起的中國城市吸引了庫哈斯的關注。2000年後,庫哈斯將城市發展課題的論述目光轉移到亞洲,不僅帥專業團隊針對深圳提出了《大躍進》(Koolhass, 2002a)一書的觀察,其2008年北京的中央電視臺大樓,再次將其論述與建築實踐相互連結,而作出激進的對話。庫哈斯對中央電視臺提出的大膽設計,在北京奧運籌辦期間引發大量的批評,針對其建築表現是否足以「威脅」北京歷史城市、文化、傳統與認同等課題的質疑,庫哈斯認為,即使是在通屬城市中,也存在著認同。但由於人們是以歷史城市作為參考典範,以至於認為大多數的通屬城市是毫無品質可言的。事實上,若是打破了對「認同」單一而本質傾向的解釋,則可以挖掘出許多新的品質,重要的是要去抓取不同形式的認同。例如,在新加坡、深圳均有其特殊的認同,僅將其視為次級城市、毫無城市品質,是太過簡化的看法(夏思藍,2003: 102)。
庫哈斯曾經在與建築系學生演講與對談時直言,建築是個危險的行業,因為這個行業有著難以置信的、困難的、甚至使人筋疲力竭的特性。這個職業也是一種令人討厭的混合物,因為既無所不能,卻又無所能(poisonous mixture of impotence and omnipotence)。庫哈斯這麼說的關鍵在於,不論建築師多麼地自命不凡,其建築與設計實踐仍是必須屈服於整個大都會的情境中,與之相比,如何能夠呼風喚雨的建築師也不過是種專業技術上的神話。
庫哈斯對於建築師的「失能」狀態,向來直言不諱,例如他曾在接受訪談時指出,「我們都承受著一種介於建築師的神話般角色和其實際作業的真實情況之間的差距。在真實狀況和這項專業自以為倚仗某種其實早已喪失的權力(不只是在技術層面,亦在意識形態,甚至藝術層面上)。」(夏思藍,2003: 22-23)庫哈斯甚至指稱,相對於城市,建築師只是在模仿著一種反建築美學的行徑,他以「反米達斯」(anti-Midas)來比擬這個現象,在神話裡,米達斯有點石成金的能力,建築師的反米達斯則說明了「所有我們碰觸之物則日漸毀壞,終至無用。」(夏思藍,2003: 22-23)庫哈斯此論形同解構了建築師「建造」的本質,他甚且以「垃圾空間」(junkspace)這樣的字眼來描述。他認為,現代建築的「發明」雖然訴諸於啟蒙的理想,但到了我們的時代,卻淪為創造了垃圾空間。
垃圾空間是我們當前成就的總合。我們建造的量遠超過過去所有世代的總和,但我們卻無法達致與它們同等的規模。我們並未留下金字塔。根據一種新的、醜陋的準則,在21世紀已經有更多的垃圾空間正在建造中,遠比從20世紀留下來得還更多。在20世紀發明現代建築是個錯誤。建築在20世紀消失匿跡了。我們在顯微鏡下閱讀這些次要的東西,希望他們可以變得新穎。我們對於群眾的關切已經讓我們無視於人民的建築。(Koolhass, 2002: 175b)
庫哈斯對「建築師」的可能角色與能量仍是立基於其對當代城市發展的觀察及分析,與其說他全然質疑建築師的存在,不如說他主張建築師應該有此自覺,而轉型為積極重新看待自身存在的專業想像。他在某次接受訪問時提到,「一個建築師有兩種工作型態模式,一種是具體明確地回應業主需要與要求;但另外一種則是關切業主所提出的問題,並加以重新闡述。」(Fraioli, 2012: 114)是否能夠重新闡述問題,為建築師當代專業實踐的關鍵。在庫哈斯的闡述中,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為壅塞都市中的一角拼圖,庫哈斯的城市論述和北藝中心、與臺北市的都市發展軌跡的關係,如前所述,劍潭一帶跨越了百年來的都市發展片段,被不斷地累加在都市地景的文化層疊中,從最初的廢河道、市集、夜市,交通運輸樞紐、一直到文化藝術表演中心,其促成與周邊的國宅、學校與劍潭捷運站體等等,和北藝中心巨大量體所共同構成的大都會地景。
在這個地景圖像中,每一座建築都不是主角,任何一棟建築物都只是構成整體壅塞文化的一份子,這是全球城市文化的共同性格,更是21世紀建築面臨的宿命,建築師已經不是掌握全局的唯一英雄(雌)。換言之,從臺北市政府的城市治理角度,企圖透過文化與設計來引導都市再生的軌跡,藉由地標性建築具支配性視覺的建築美學創造都市文化資本,在地的歷史脈絡必然產生的作用能量,是不容忽視的,而這也可以從北藝中心量體的植入,及其與士林夜市、劍潭捷運站等都市景觀相互間的對應關係來觀察。
建築量體與士林夜市的戲劇性言說
以庫哈斯對城市與建築師專業實踐兩條分析軸線來看,在這次的設計案中,依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設定的空間計畫,包含一座1,500個座位的劇場,以及兩個800個座位的球型鏡框及多元式的中型劇場。三個劇場以一個相當誇張的球體、方體彼此鑲嵌,暗示了這些劇場平日雖相互獨立,但也可能彼此聯通成為一個共同的空間。但這幾個幾何量體的組構,形成一個外型突兀的龐大量體,夾在劍潭捷運站與士林夜市之間僅2公頃的的狹小基地上。
根據設計團隊陳述,這三個劇場彼此之間可以相互連結或獨立運作,凸顯了新的、實驗性的表演藝術的可能性。在劇場旁提供的公共的穿越通道,讓觀眾可以參觀後臺區域的狀況,構成獨特的表演準備空間與互動模式;之所以提供一個如此具有觀看與視覺經驗的互動空間,來自於設計團隊希望可以跟緊鄰的士林夜市的視覺感受相互連結,提供充滿在地日常生活與大眾活力面向的戲劇感。易言之,看與被看之間,這個量體重新界定了士林夜市與北藝中心的對話關係。以庫哈斯向來擅長創造話題、凸顯建築師在這個設計全球化過程中擁有的表現性。設計團隊指稱,這個球體的設計概念的靈感來自於在夜市看到的攤車鍋具,而臺北市這個晚睡的城市,經由螢幕上可以投射影像,使得夜市生活與螢幕表現出來的戲劇性,構成一個看似相當弔詭的都會意象,卻也再譯了臺北都會形象與市民日常生活的內容,與其可能創造出來的空間經驗。
另一方面,從都市整體景觀與周邊地景來說,其量體置放在劍潭捷運站旁,劍潭捷運站以其高聳的懸吊結構,在庫哈斯的量體前顯得渺小極了,這對已經習慣中山北路四段、捷運劍潭站周邊支配性景觀的市民來說,新的建築量體看來儼然將重新改寫地方的紋理與都市景觀。亦即,一個新的臺北都市意象會經由這個名牌建築來重新定義。我們或許重新回溫了庫哈斯對紐約曼哈頓「壅塞」文化的迷戀,以在大都會的混亂氛圍中,藉由夜市的生活地景,訴說臺北版本的奮發向上;也可能是提供了臺北在這個全球化時代,經由名牌建築的龐大造作,登上視覺化排行榜的話題。
(本章未完。本文由典藏藝術出版授權發布,節錄自《在建築與文化之間,我們設計》一書,惟段落經編修,欲閱讀完整文章請參考本書。)
